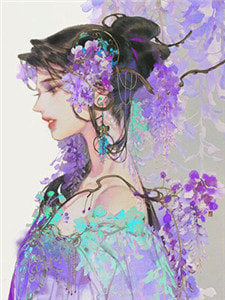>绿意盎然的郊野意外地迎来了一抹红,夹肠小道上,一方点缀着红绸喜布的大红花轿颤颤悠悠地由远抬近。
从守轿的喜婆到抬轿的轿夫,皆是行色匆匆的模样。
可他们面上不仅不见喜色,反而流露些许慌乱仓促的表情。
突然,轿夫脚下一个不稳,磕绊得险些摔倒,也让平稳的轿子骤起颠簸。
那喜婆压低了声音气骂道:“手脚利索着点!要是把事情办砸了叫闻老爷怪罪下来,可没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轿夫连连应了几声,再起轿时手脚拿捏得又平又稳。
不过经过方才那么一颠簸,轿子里的人却是被震得从昏睡中清醒。
闻依澜睁开眼的时候,头上盖着一条喜帕,入眼是鲜艳的红。
她伸手去摘,却发现双手被粗绳捆得结结实实,似乎唯恐被人看见落了口实,还欲盖弥彰地罩了一条红帕遮掩。
闻依澜的嘴里被塞着白布,呼救无门,垂眼见自己身着鲜亮嫁衣,一股浓烈的恨意油然而生。
郡城闻家乃是有名的书香世家,家主闻承博又是当朝太傅,与皇家关系甚笃。民间更传,闻家家风严正,廉洁清白。
可谁能想到,闻承博披着一张道貌岸然的伪善皮,竟会纵容家丁将闻依澜这个嫡女打昏,代替她那个刻薄的庶出长姐出嫁?!
想起自己因为操持闻家过劳而病逝的生母,闻依澜泛红的眼眶中浸润了泪水。
娘,您的一片情衷,终究是所托非人了……
花轿被人一路从郡城抬往了空山附近的村镇,穿过了空山集,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了上去。
陡峭的山路让试图挣脱绳索的闻依澜一后脑勺撞在了木板上,两眼一阵发黑。
好痛!
她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
走了这么远的路,又闻山风呼啸、鹧鸪鸣叫,莫非……她这是进了山里?
等等!之前听闻长姐的未婚夫婿虽是皇家子嗣,却因年幼起便体弱多病,因而远离郡城王宫,深居世外疗养……
她这是代替长姐嫁到了什么穷乡僻壤之处吗?!
轿子往地上重重一磕,闻依澜身形歪斜一晃,还未来得及坐回正身,便觉花轿的门帘子被人掀起。
那喜婆见她竟挣扎得把红盖头都甩到了脚边,忙拾起来拍去上面的尘土,在闻依澜的怒视下,给红着眼圈瞪着湿漉漉杏眸的她重新盖在了头上。
喜婆嘴碎地念叨着:“闻二小姐你可别怪老身!要不就说这人各有命呢?闻老爷给您安排这婚事的方式许是有些不妥,不过您这夫婿可是这十里八乡的俊相公、不亏!”
她这话刚说了一半儿,便被蒙着盖头的闻依澜重重地踢了一脚,竟是被直接踢出了轿子外!
恰逢云清和被贴身老仆耳提面命地催促着出门接亲,刚走出来,便看见喜婆吃瘪挨踹的这一幕,那张一贯平和冷漠的脸上,眉梢微微挑起,饶富深意。
好凶悍的新娘子!
他很快便又恢复成无喜无悲的模样,垂了眉眼,踱步行至花轿前。
“你这个丧……”喜婆本是想破口大骂几句好解解气,谁想当那一双厚厚的长靴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喜婆当即扭曲着脸把那几句难听的脏话又咽了回去。
只见她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发福的身材竟透着几分狡诈的灵活。
尖锐的嗓音在耳畔响起,直穿脑膜,叫云清和不悦地拧起眉峰。
“哟!这位就是新郎倌儿吧?哎呀、果然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啊!新娘子是得有多大的福气才能寻着您这么好的人家……”
云清和冷冷开口:“你要是再废话,就直接把她抬回去吧!”
那喜婆瞬间偃旗息鼓,像赶瘟疫似的把闻依澜从花轿里连拉带拽地接出来。
目不能视、口不能言的闻依澜光从这只言片语中就能听出来,这门亲事是男方也不待见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出圆了这门亲事呢?
喜婆像是要把方才被踹的糗事报复回来,恁大的手劲儿抓着闻依澜的胳膊,生怕她跑了似的勒得细臂生疼。
那喜婆怕男人察觉到闻依澜的不对劲,匆匆送闻依澜进了屋子,连喜堂也顾不得叫拜,便匆匆带着几个轿夫飞也似的离开了。
闻依澜被安置在一处空间狭小的房内,鼻尖下充斥着一股浓郁的药味,看来长姐未婚夫婿是个短命的病秧子一说,并非空穴来风。
——不,现在是她的夫婿了。
一想到以后的日子要和一个处境比自己还要凄凉的男人度过,闻依澜就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突然,冰凉的触感从闻依澜的手背上轻轻滑过,喜帕被一只手掀起。
被绳索捆缚的双手就这么呈现在对方的面前。
云清和意味不明地轻哼一声,低声道了一句:“果然!”
云清和的眼力很好,从见到闻依澜的第一眼起,她身上各处别扭的细枝末节都没逃过他的眼睛,这也让云清和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这个小新娘,是被绑来的。
“当初是你们闻家厚着颜面向圣上求赐姻缘,无非是看重皇家的荣华富贵与位高权重。可如今我不过是个被遗弃的落魄皇子,你们闻家便避我如蛇蝎。”
“怎么?嫁与本宫,让你闻家大小姐抬不起头了吗?”
半晌,盖头下的人都没说一句话,不知道是心虚还是害怕。
云清和不悦地拧了下眉头,一把将闻依澜头上的红盖头掀起,露出了一张泫然欲泣的娇俏面容。
一双水汪汪的潋滟杏眸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她,盈盈水光微漾,这一眼几乎看到他心坎儿里去!
久违的,云清和感觉到如同一潭死水的心蓦地颤动。
然后,他的目光便落在了她嘴里被紧塞的白布上。
也难怪她不说话……
闻依澜看着渐渐走近的云清和,怕得全身都在哆嗦。
眼前的男人相貌称得上是俊美无俦,五官清明硬朗,身形精瘦,即便是一身略显质朴的细布白衣也遮掩不住他不凡的贵气与傲然。苍白的面色带着点恹恹的病相,缓和了几分他凌厉眉眼带来的威慑感。
可闻依澜还是打心底里发寒,原因无他。
她自幼便能透过外表,看见别人的心会呈现出或红或黑的颜色,它们分别代表着存有善念与恶意的两种截然不同之人的真实心理。
而云清和胸膛里的心脏冒着熏天黑气,几乎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其中!
这家伙分明就是……大魔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