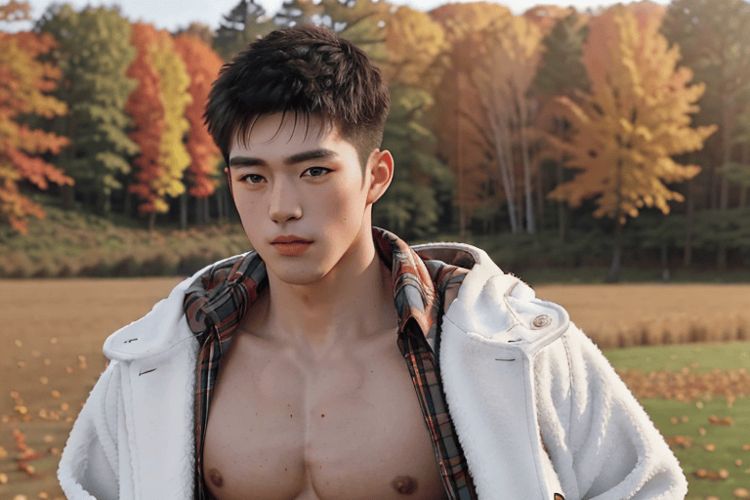我望着她精致的脸,嗤了一声。
忽然想起初见她那日。
她第一次参加名流拍卖会,被自己的姐妹戏耍,穿着不合身的礼服,站在聚光等下,像只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
“陈小姐,您答应拍卖的翡翠镯子,经鉴定,这是赝品!”
拍卖师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在宴会厅里回荡。
瞬间,窃窃私语如潮水般涌来。
陈萱的脸色瞬间煞白。
我悄悄去了后台,掏钱替她解了围,才让她逃过一劫。
虽然她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但我的确是因为同情而记住了她。
以为是个好的开头,没想到是悲剧的伏笔。
......
“苏宴!你倒是说话呀,装什么死?”
女人终于不耐烦了。
她今天画了精致的桃花妆,眼尾贴着细小的水钻。
二十三岁的年纪,美得惊心动魄,也冷得彻骨。
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医生说我现在不能......”
“闭嘴!” 她把手机狠狠砸在我腿上,“不就是受点委屈么,你就玩消失?”
“这几天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你都不接,你怎么不想想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我才需要找别人?”
我冷笑,没再接话。
她看我不如往日那般舔自己,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语气软了几分,“好了好了,给你个将功赎过的机会。”
她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上的钻戒。
“爱马仕那款鳄鱼皮铂金包今天截止付款,你现在立刻让人去专柜,务必在下午三点前把包拿下。”
我突然觉得无比可笑。
三天前她当众毁了我的尊严,现在却理直气壮地来找我要钱买包?
“多少钱?” 我的声音冷静到不正常。
“才九十八万。”她撇撇嘴,“快点转钱,我约了徐少七点吃饭呢。”
我缓慢地抬起还在输液的手,指向床头柜:“钱包在那里,自己拿卡。”
她眼睛一亮,动作熟练地抽出黑卡塞进自己包里。
临走前终于想起什么似的,敷衍地摸了摸我的脸:
“好好养病,别总让我操心。”
第一次觉得她身上的香水味浓得令人不适。
在她转身的瞬间,我突然开口:“密码是陈墨的生日。”
陈萱猛地僵住。
转过身时,眼里带着一股狠戾,“好端端的,提那个贱人干什么?”
“没什么。” 我慢悠悠道,“只是突然想起来,你好像从来不知道,陈墨是我未婚妻。”
“你......你说什么?”
陈萱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尖得刺耳。
走廊上路过的护士都忍不住探头张望。
“不可能!”
“那个冒牌货早就被赶出陈家了!她算什么东西!”

陈萱见我态度冷漠,又嗤笑道:“苏宴,你舔人已经舔到这种分不清好歹的地步了么?”
“那个贱人抢走了我二十年的人生还不够,现在还要抢我的男人?行啊,那也得看看她有没有那个本事!”
我终于忍不住出声:“你的男人?这三年来,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人看过?”
我拿起手机点开一个视频文件,“要不要看看你在闺蜜群里怎么评价我的?”
“那个暴发户土包子,要不是看他舍得花钱,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这是你的原话吧?”
她的瞳孔猛地收缩。
没想到我竟然会有这些信息。
她一个在底层活了十几年的人,怎么会知道豪门圈的尔虞我诈?
这些,都是她那些所谓的‘闺蜜’林夏羽发给我的,目的,可想而知。
人人都想要得到资源和财富,自然谁都可以是踏板。
上一世我对她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妄想能感动她。
可这一世,我忽然就没有这种愚蠢的想法了。
“陈墨不一样。”
我故意用温柔的语气,“她从不会在背后叫我土包子,也不会把我送的礼物转手挂二手网站。最重要的是——”
我凑近她惨白的脸,“她是不是陈家真正的血脉无所谓,你,也不过是个冒牌货。”
“你胡说八道什么!”陈萱突然暴起,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就往我头上砸。
杯子砸在墙上,碎片弹开,割破了我的脸。
血滴在雪白的床单上,格外刺眼。
陈萱踹翻了椅子,满意地笑了:
“追我的人,从港城排到了法国,苏宴,你别后悔,再来求我,我连个眼神都不会施舍给你!”
她走后,我盯着天花板发呆。
突然想起陈墨被陈家赶出门的那个雨夜。
她浑身湿透地站在我公司楼下,“苏宴,我不是陈家的千金了,我们的婚事......”
我当时因为对陈萱的迷恋,只跟她说,“我从来没当真。”
那毕竟是长辈在喝酒时口头应下的婚事,陈老本人都不在意。
我又怎么会在意?
如今,我慢条斯理地从枕头下抽出手机,
给陈墨发了信息:“婚礼都准备好了,还缺个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