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景总说,他那留洋归来的女兄弟宋和音思想新派,与我们这些深宅妇人不同。
母亲病危那日,我跪着求他回府,他却搂着宋和音的肩,在青楼高谈“家国大义”。
后来,宋和音撺掇将我母亲火化。
我去讨要骨灰时,正撞见他们在雪地里嬉笑追逐。
容景嫌我“晦气”,当众命人将我杖责。
板子落下时,我护住小腹,却仍没保住孩子。
鲜血浸透素衣那日,他跪在婆婆面前:
“求母亲准许,贬妻为妾。”
我笑出了泪,摘下簪环,自请下堂。
后来,容景夜夜守在绣坊外,淋着雨求我回头。
只可惜,我早已不是笼中雀,
而他,再够不着我的天。
……
“少夫人,这已经是派出去的第十批人了,少爷……还是不肯从明月阁回来。”
小厮跪在地上,声音颤抖。
我站在主院的窗前,手指紧紧攥住窗棂,指节泛白。
贴身丫鬟春红站在我身后,声音里带着哭腔:
“少夫人,亲家太太的状态越来越差了,府医说……怕是撑不过今晚了。”
我回头望向病榻上的母亲。她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颤动,似乎在低声呼唤着什么。
我走近几步,才听清她在唤着“容景”的名字。
容景是我的丈夫,七日前,为着他的女兄弟宋和音,容景与我爆发争执,负气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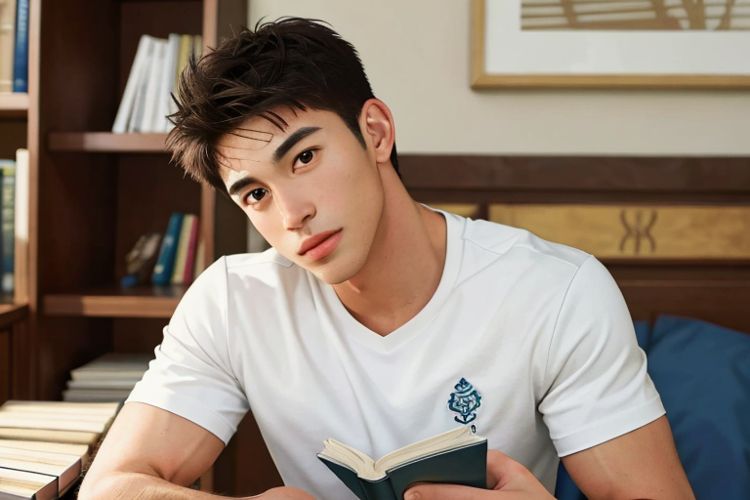
想到此处我心口一阵刺痛,仿佛有无数细细密密的针扎在心头。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压下那股翻涌的情绪。
“去把我的斗篷拿来。”我忽然开口,声音冷静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
“少夫人!”春红惊呼一声,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您……您怎么能去那种腌臜地方。”
“是啊,少夫人三思!”一旁的丫鬟小厮们也纷纷跪地。
我扫了他们一眼,目光冰冷:“都让开。这是母亲最后的心愿,我一定要替她完成。”
“可是……”春红还想再劝,却被我抬手打断。
“没有可是。”我语气坚决,转身大步走向门口。
明月阁里,等待已久的小厮引着我去了容景的包房。
“容大少,你家那位可真是够粘人的,一连派了十来个小厮喊你回去,等下不会亲自上门来吧?”
还未踏进包房,我便听见容景友人的调笑声从门内传来,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
容景的声音懒洋洋地响起:“她从小最重规矩,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她啊,怕是连明月阁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夜风拂过,一阵脂粉香气混杂着酒气和丝竹声,熏得我一阵眩晕。
这样的地方,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踏足。
可一想到病榻上奄奄一息还在等着见容景最后一面的母亲,我便咬紧了牙关。
便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阿姐,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容景见到我,显得极为震惊。
我比容景大三岁,又是他的奶娘所生,所以容景从小便唤我阿姐。
“天呐,这不是最重规矩体面的绣芸嫂子吗?居然醋性大发追到这里来了。”
一道略显惊讶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我认得她。
宋和音,容景最近结识的“女兄弟”。
她上了几天洋学,便口口声声喊着“女性解放”,成日和容景几人厮混在一起,出入风月场所如家常便饭。
我曾委婉地向容景提过几句,觉得女子不该如此抛头露面,更不该混迹于这种地方。
可容景总是轻描淡写地敷衍我:
“和音上过洋学,思想先进,和你一般的后宅女子不同。”
当我再想多说几句时,容景便不再理我,要么转身离开,要么低头看书,仿佛我根本不存在。
自从宋和音出现后,容景与我的关系便不似从前和睦。
未等我开口,宋和音便轻笑一声,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
“她为什么来?来逮你的呗。”
她斜倚在软榻上,目光轻飘飘地扫过我。
“阿景,你的女人一天天就没别的事做了吗?”她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嘲弄,
“先是派了一堆小厮来寻你,现在又亲自找上门来扰我们兴致。要我说,这些后宅女人真是无趣至极。”
她说着,随手拉过旁边一个男人,指尖轻轻抚上他的脸颊,动作轻佻而自然。
“这女人啊,就该学点新思想。”她抬眼看向我,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整天吊在一个男人身上,有什么意思?”
“和音,你做什么?”容景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悦。
他大步走过去,一把将宋和音从那个男人身边拉开,拽到自己怀里。
宋和音顺势靠在他胸前,仰头看着他,眼中满是戏谑:“怎么,吃醋啦?”
她的目光越过容景的肩膀,直直地看向我,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
我不再耽搁,仔仔细细将母亲生病想要见他最后一面的消息告知。



![[看见弹幕后拳打极品一家,脚踩假千金,男主当狗溜!]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胡子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963762abe508978bf14de0b3d9be55bec90a02638f476-Y0Vv52_fw480webp.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