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呢?”
我听见自己哑着嗓子问。
林俊辉愣了下,转身从布兜里掏出团血红的东西。
牡丹金线上缠着泥浆,盘扣崩得只剩两颗。
他低头拆线头的样子,像极了我们头回约会时,笨手笨脚给我编麻花辫的模样。
“赶明儿再给你做十件,挑苏杭的软缎......”
他的声音突然哽住,手指深深陷进绸布里。
我偏头看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一只湿漉漉的麻雀撞上玻璃,扑棱着栽进了积水里。
天亮了。
林俊辉还趴在床沿熟睡,左手还死死地攥着我的被角。
"吱呀"一声,护士推着药车进来,铁盘上的搪瓷缸叮当作响。
林俊辉猛地惊醒,下巴磕在床栏上"咚"的一声。
他胡乱抹了把脸,从铝饭盒里舀出白粥:"静怡,趁热......"
瓷勺磕到我的牙齿时,我闻见了他指缝里的茉莉香。
昨晚他借口去厂里值夜班,白衬衫领口却沾着半抹嫣红,像是女人蹭上去的口脂。
"慢些喝。"
他掏出手帕给我擦嘴角。
走廊忽然一阵哄笑,几个小护士推着轮椅从门前经过。
"林厂长好福气哟!"
最胖的那个探头揶揄,"新娘子穿旗袍的模样真真赛过挂历明星!"
后面的话被同伴掐断了,轮椅轱辘碾过了我的影子。
林俊辉的手抖得厉害,粥泼在被面上,洇出了黄褐色的印子。
我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搪瓷缸。
"婚书......"
我望着缸底沉淀的药渣,"不是说今天去领吗?"
他霍然起身,铁架子床跟着晃。
玻璃药瓶叮叮当当撞在一起,倒映着他仓皇翻找公文包的侧影。
大红烫金纸展开时簌簌作响,我盯着"张静怡"三个字,金粉扑簌簌地落在被褥上,像极了撞车那日飞溅的碎玻璃。
"等你能坐起来了,咱们就......"
他话音未落,走廊传来尖利的争吵。
老医生扯着嗓子骂:"胡闹!试个衣裳要占三间诊室,当医院是百货大楼?"
我伸手抚过婚书上的鎏金花纹,指尖突然传来刺痛。
翻过来看,背面蹭着一半枚玫瑰色唇印,边缘晕开淡淡的水痕,是眼泪的形状。
林俊辉劈手夺过婚书,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定是办事员粗心......"
话音未落,门外"哐当"一声,大红绸缎从推车上滚落,旗袍上的珍珠扣子蹦到我跟前,骨碌碌地转着圈。
"苏小姐非要在医院试旗袍......"

小护士的辩解被高跟鞋声打断。
苏婉仪倚着门框拢头发。
看到我后,她冲我晃了晃请柬,烫金"新娘"二字晃得人眼疼。
"静怡姐,俊辉怕你伤心,所以才求我替你去礼堂走个过场。"
她腕上的金镯子叮咚作响,正是林家祖传的那对龙凤镯。
去年除夕,林母说要等我过门再给,此刻却死死地咬在她雪白的腕子上。
林俊辉低着头一言不发。
"俊辉,旗袍腰身紧了。"
苏婉仪娇嗔着转圈,经过我时,还瞥了一眼我的石膏腿,"你昨晚量尺寸时手在抖什么?"
她颈间的红痕若隐若现,恰巧露在护士推来的穿衣镜里。
镜中映出我蓬头垢面的模样,在这个时候显得有些可笑。
林俊辉突然暴喝一声"够了",他的拳头砸在镜面上,裂纹蛛网般爬满苏婉仪笑盈盈的脸。
老挂钟敲响十二下时,我终于摸到了护士站的电话。
转盘硌着我的手指头生疼,我对着听筒说"要殡仪馆",值班护士吓得打翻了紫药水。
林俊辉冲进来抢话筒,我死死地咬住他的手背,一股咸腥味在舌尖漫开。
"静怡你听我说......"

![[我截肢那天,丈夫的私生子上了族谱]大结局](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7e4990ef420594521d042b9319aacd8.jpg)

![[死后第五年,老公为救恩人再次典当我的寿命]小说全文txt完整版阅读-胡子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3b89c0bd42dbca3e965fd6ace8b4efe.jpg)
![[人间捉鬼师]最新章节列表_[江浔才]完结-胡子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aec379310a55b3194e437e32e7c86b2acefc17a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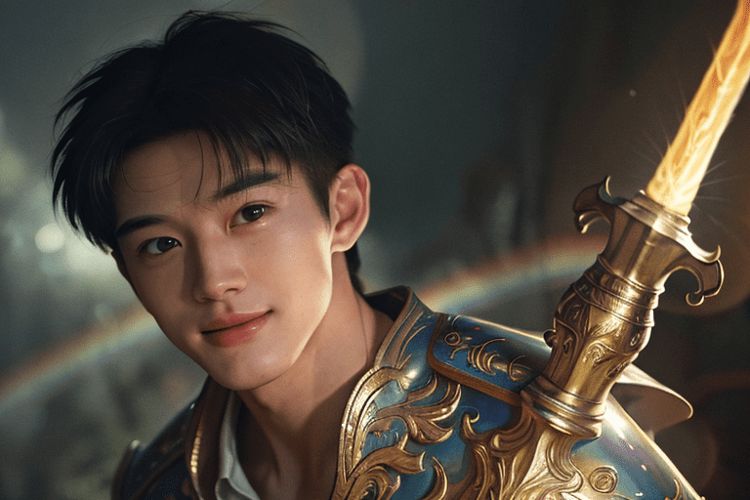
![[弟弟升学宴上,我提出断绝关系]最新章节列表-胡子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ff1ee2e793990f255caa46dfbc7c43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