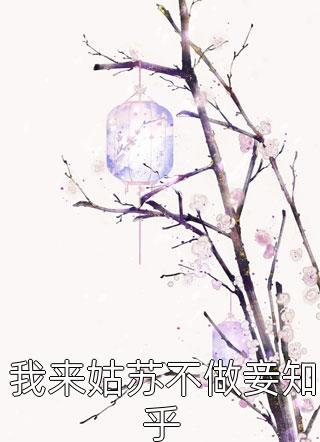我十四岁的时候,挂牌子了。
阿母亲传的琵琶手艺。
她每次听我弹唱,都说我唱的弹的都有新意,是天生的艺人。
阿母喜欢我,客人们也喜欢我。
阿母说,要我耐住寂寞,不要因为这里客人撒下的大把金银沉迷,她自会为我寻良人。
我说,阿母,我不愿嫁人,真的,我就想弹琵琶唱小曲儿,直到头发都白了。
姐妹们笑我言辞新奇,思想古怪。
到了我们这一辈儿,上一辈儿挂牌子的姑娘们几乎都被客人赎身走了。
就只有一个,叫春满的姑娘,她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有烟霞癖,却依然留在琅坊里。
她的客人越来越少了,而她满不在乎,好在阿母并没有因此而轻待她,还给她安排了其他活儿,让她没事儿去教小姑娘们唱曲儿。
燕生长大了,他再不像是当初我于大街上遇到他那副干净温柔的挺拔少年模样。
我也长大了,我十五岁了,抱着琵琶满怀欣喜地去见他,阿母为我开门之前告诉我,里头是大茶商陆家的公子。
阿母说,那是位风华正茂的公子,你好好唱。
我抱着琵琶,小步躞蹀地迈进屋子,见到他。
我问他好,陆公子。
他旁边还有其他公子,我不认识,于是笑一笑:「你们好。」
这句话不合适,而我确实想说。
果然燕生看了我一眼。
但他依然不知我是谁。
无妨,真的无妨。
我坐在他们旁边,将琵琶弹得铮铮作响,可就是不唱。
我盯着燕生仔细地看。
他真的长大了啊,坐在酒桌正位,身旁三两好友,谈笑风生,他身姿挺拔,容貌英俊,身着绣黛竹的长衫马褂,手中把玩着一枚玉佩。
眉眼清澈,彬彬有礼,真称得上风华正茂,芝兰玉树。
他侧过头来看我一眼:「什么曲儿啊,从未听过。」
我笑,明媚极了,因我开心。
我说,这是未来曲儿。
他也笑,温柔道:「你叫什么,挺有趣的。」
我看着他:「年年」
「年年?」他好奇。
我告诉他,因是过年时被卖进来的,所以,阿母给我起名字叫年年。而我并不难过,因我喜欢唱歌儿弹琴。
曲儿弹完了,他与酒桌上的朋友并不轻浮地向我凑近,依然是坐在那不远处与我讲话。
他朋友问,年年,你觉得我们这些人,哪个你最喜欢啊?
我抱着琵琶,看过去。
这四个人,都是青年茂盛的少爷公子,穿戴皆不差的,他们言笑晏晏,便是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可若问喜欢,我却都是不喜欢的。
那三个,我不认得,那一个,我认得,可他不记得我。
我说,我最喜欢我自己。
燕生像是意外:「为什么?」
我面对着他,有着我的勇气:「因为我活得艰难。」
「苦太多了,若不爱自己,活不下去。」
那一场儿在门外酒女的嫣然笑语声中结束。她们进屋子来,我抱着琵琶,走出去。
迈出门,我回头看他一眼。
他没有看我,但也没看那些酒女。
我知道,他是不同的人。
对我而言,不同,对来这琅坊的客人,也不是同路人。
那之后过了两三年,我都没再见到他。
不过我十八岁的时候琅坊出了一件大事。
姑苏大茶商陆家倒了。
倒得突然,说是陆家老爷子茶山上死了人,官家的来查,牵出了老爷子给沿路运茶官路上的人使了暮夜金,谋取私利。
这事情一出来,牵扯颇多,老爷子判了秋后问斩,太太殉情,鼎盛陆家,倒台了。
茶山全然充公,陆家私财更是一分不剩添了外债。
陆家二姑娘本来好好的一门亲事,也因这件事儿黄汤了。
这样大的变故,吓了我一跳。
当夜我偷偷出了坊,往那陆家去。
陆家的疮痍颇大,空荡荡连个仆人都不见了。
门没人守,我拥门进去,月明星稀,夜凉如水,大院儿安静得如无。我见到他身影瘦削地坐在院儿中,怀里抱着爹娘的牌位。
这偌大宅门,不复往日热闹,竟萧索到这般地步。
我走过去,静悄悄地,听见他说,只剩下这些了。
我问:「剩下什么了?」
他根本不知道我如何进来的,而他也全然忘记了我是谁。
可他没心情了解我,他说,只剩下我爹娘的牌位。
我怀里揣了个小盒子。
那是我刚才偷从坊里跑出来时拿的,是我这些年来收的客人银票。
我蹲下来,在他身旁,将手中盒子递给他,我说,人有志,便不怕从头来过。
他漠然,接过盒子,打开,见到银票又狠狠关上,丢给我,凶问:「你是谁?!」
我被那盒子砸了脑门儿,很疼。
我木木的,我是年年。
他完全没有印象:「年年是谁?」
我并不觉得耻辱:「是琅坊弹琵琶唱小曲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