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婶子离开小院时,天边为数不多的几道残红也被压抑的黑色吞没了。
正屋中央,陈旧斑驳的木桌上新添了牌位,香炉两旁,在秋风中颤动不休的烛火努力驱逐着无孔不入的黑暗,为蒲团上的小姑娘撑起了一小片昏黄脆弱的天。
周遭静得只剩“簌簌”的风声,还有她微弱无助的抽泣。
一身粗布麻衣的若梨紧紧抱着一卷明黄色的,与这屋子格格不入的锦帛,双腿屈起,尽可能地将身子蜷缩起来。
这已经是母亲过世的第七日。
先前来吊唁的那位大人说,母亲下葬后他会派人来接她,将她收养于自己家中,以报父亲对他的救命之恩。
若梨只需要带陛下的追封圣旨。
泪水被风吹凉了,干在脸上不大舒服,冰凉的指腹刚触到眼底温热的肌肤,她细瘦的身子便哆嗦了一下。
牙关轻咬,若梨再次将手指贴上去,忍着冷把泪揉干净。视线清晰起来后,她再次看向在风中“嘎吱”作响的陈旧院门。
父亲上战场前,门从不会这般响的。
想着,小姑娘的眼睛又酸了起来,可这次她没有再哭。
这些天帮着料理丧事的张婶子说,要收养她的大人出身名门,日后她在那大宅院里的生活不见得容易。
不知过了多久,耳畔依稀传来马蹄声,可是又和先前听过的不一样。不密集,也不沉重,均匀平稳。
声音越来越近,而若梨蜷缩着的腰背也不知不觉放松,她直起身子,酸麻的小腿缓缓舒展,一双眼眸亮得揪心。
等待的时间不长,可忘记眨眼的若梨煎熬得厉害。
当她再睁开眼时,那通体棕红的小马驹已经停在了矮矮的篱笆墙外,在原地打转。
月色下,白色披风在晚风中张扬鼓动,上面流转着粗布麻衣所没有的光泽,流畅而鲜活。
披风的主人没有立刻下马,他低着头摸了它片刻。许是察觉到若梨的目光,他侧首看向昏暗的院子。
两个孩子的视线遥遥地交错,却不曾有什么复杂的纠缠。
若梨眨了眨酸痛的眼睛,而身披白色,却依旧贵气夺目的少年也踩着马镫翻身下来,动作利落,又是她形容不出的好看。
木门被他推开,伴着尖锐的“咯吱”声,少年的眉拧了拧,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一眼,顺便用手将它扶住,阻止了之后的刺耳声音。
夜色下,他的神色若梨看不清楚。
垂下眼帘,她看向怀中明黄色的锦帛,细嫩的五指收紧,将一小截粗糙不平的衣袖卷进掌心。
他的衣服,还有这卷圣旨所用的料子都是若梨从未见过,摸过的。踩着落满银辉的青砖,少年一步步走向简陋的正屋,瘦削的腰杆挺得笔直,头却微微低着,眸中完全倒映出屋内的陈设时,他多少有点讶然,又很快收敛。
跨过门槛后他没做停留,径直走到若梨面前。
就在小姑娘要抬头时,少年弯腰蹲了下来,手肘支着腿,许是觉得这样仍不舒服,他的膝盖自然地落在泥泞冰凉的地上,将马鞭随意放到一旁。
“路不熟,来晚了点。”“你跟我走吧。”
上下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小姑娘,少年好看的眉又一次皱了起来。她怎的这般羸弱。若梨抱着圣旨的臂膀已然收到最紧,可她的心脏还是“砰砰”跳得厉害,完全无法安定。
她突然很害怕离开。可她答应了娘,要努力活下去。
“你,你的衣服脏了......”小姑娘嗫嚅着,只怯怯地望着少年拖到地上,扫了些许灰尘的披风。
“小事。”“我姓裴,名屿舟,以后就算是你哥哥了。”
摆了摆手,少年说完后便站了起来,朝地上的若梨伸出手。
他的五指修长白皙,骨关节分明又硬朗,却并非她想象中的平滑。有些意外的若梨看向少年,再次被卷入他的瞳孔之中。
那是她向往,却与之甚远的矜贵,坦然。
尽管她的手不脏,但抬起来前,若梨还是小心地在粗硬的麻布衣上蹭了蹭,而后才缓缓探出袖子,朝他靠近,带着几分胆怯和犹豫。
在与少年的掌心仅咫尺之距时,他突然向前主动握住若梨细软的,同样布着些茧子的小手。
“我又不咬人,你怕什么。”
微微用力,比小姑娘高了一个头还有余的裴屿舟轻而易举地将她从蒲团上拉起来。
二人的手都有几分粗粝,但一个沁凉,一个温暖。
“你就带这个?”“不过看着也没其它可带的。”
他像是说给若梨听,又更像在自言自语。
扫了一眼若梨怀中明黄的圣旨,裴屿舟竟全无在意之色,更别说敬畏,接着他便侧身环顾四周,眼中倒有了几分变化。






![[情深不绵长]最新后续章节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64a2292b1093289aa594b561d14cb71.jpg)
![[放弃白眼狼儿子]最新章节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7c115f49c00747b62364a2fb1e13955.jpg)





![长夜与风说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_[舒时吟]全文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ba5019527394456a0d90b1f7a2cbb56.jpg)
![[嫂子把女儿丢进训兽笼后,我笑了]后续大结局更新+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9657feb13f1227110a4b75e24c43f49.jpg)



![[老公的女友上门挺孕肚逼宫,却把婆婆认错成我打成残废]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daec982ce9f1d9834de528c2afdc3b9.jpg)




![我干物业的那些年后续完结版_[吕向荣]在线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6843328f427112860c707e1d33561d33f391f7c93c79c4-HlVsM7_fw480webp.jpg)

![「笑死!都领证了,渣男过来求复合」无弹窗阅读_[唐颖陆子墨]大结局](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002e19f5ea206b2a4eb3dc71711b3c0.jpg)



![[养老院失火十几个老人生命垂危,我却淡定看戏]后续无弹窗大结局](http://image-cdn.iyykj.cn/0905/9345d688d43f879417b0b2abb778e7f81ad53a5c.jpg)





![[儿子去世后,我决定离婚]后续无弹窗大结局](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3211d1b6ccd9a9d25853bf29419d24e.jpg)
![[我死在黑熊爪下,妻子却选择救她的白月光]小说全文txt完整版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f1d241353818c56cf266bb513b8fb2f3.jpg)


![[落雨成空]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681b5cfbd4840860edd68e3b37332ce.jpg)


![[小三与老公在我面前叫嚣,被我打脸了]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7cc487ae310f96633dc0270e0deae81.jpg)




![[我们输在了见不得光的那七年]完结版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cb3db5eeba88e9b7a23ea98545fb660.jpg)






![[相思相负不相见]后续完结版](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9aa9708e65844031795159ab6c07236.jpg)
![[为建设祖国,我放弃自由国荣誉身份]电子书](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b1494e3d0353a4d3d7934284b3078c8.jpg)




![[爱意成空]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2237d9ce73c107a6f6307ee5276e5a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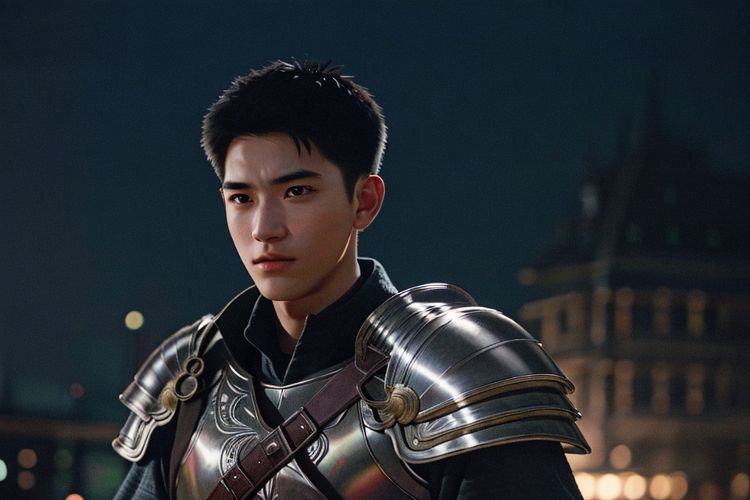


![[假千金用女儿换走了我的儿子]最新章节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1b2dfe19e4f98c5d370fc52c2295b13.jpg)
![[浮云别后十年间]最新章节列表](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51a9901537d0b03f9a88ad66d79447f.jpg)







发表评论